

当前,围绕AI制药的困境仍然是:技术上的短期炒作,难以掩盖结果上的遗憾。
近两年来,我们频繁见证AI参与设计的分子的临床失利,而这些药物进入临床却曾被视为行业的里程碑事件。
人们意识到,AI目前还无法破解当前药物研发的困局,企业们仍然对已经验证的靶点和适应症趋之若鹜,行业投入产出比仍然非常低,资本近年来也逐渐开始逃离生物医药。
本次智见栏目,智药局对话赵宇,他是哲源科技联合创始人、中科计算技术西部研究院研究员、图灵-达尔文实验室副主任。在他看来,AI赋能药物分子发现,无法弥合当前临床试验90%+的失败率。

赵宇十分认同Exscientia创始人霍普金斯的观点:如果我们想改变临床成功的可能性,不仅仅是更好的分子,我们还需要更好的转化模型。
什么是更好的转化模型?
赵宇给出的答案是计算医学,要认知疾病,认知患者,认知药物,才能成为好的转化模型。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计算医学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计算医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它代表用计算方法理解人类疾病,为疾病机制、疾病诊断和治疗提供见解。
事实是,以计算医学为思维锚点,哲源科技对于AI制药以及商业化模式都有自己的实践,其中最核心的是“AI+疾病”的药物研发导航系统,势必要从临床的角度逆向思考赋能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差异化关乎临床价值和管线商业化成功与否。
那么在赵宇看来,AI、疾病、药物研发三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AI制药痛点已经转移
AI制药痛点已经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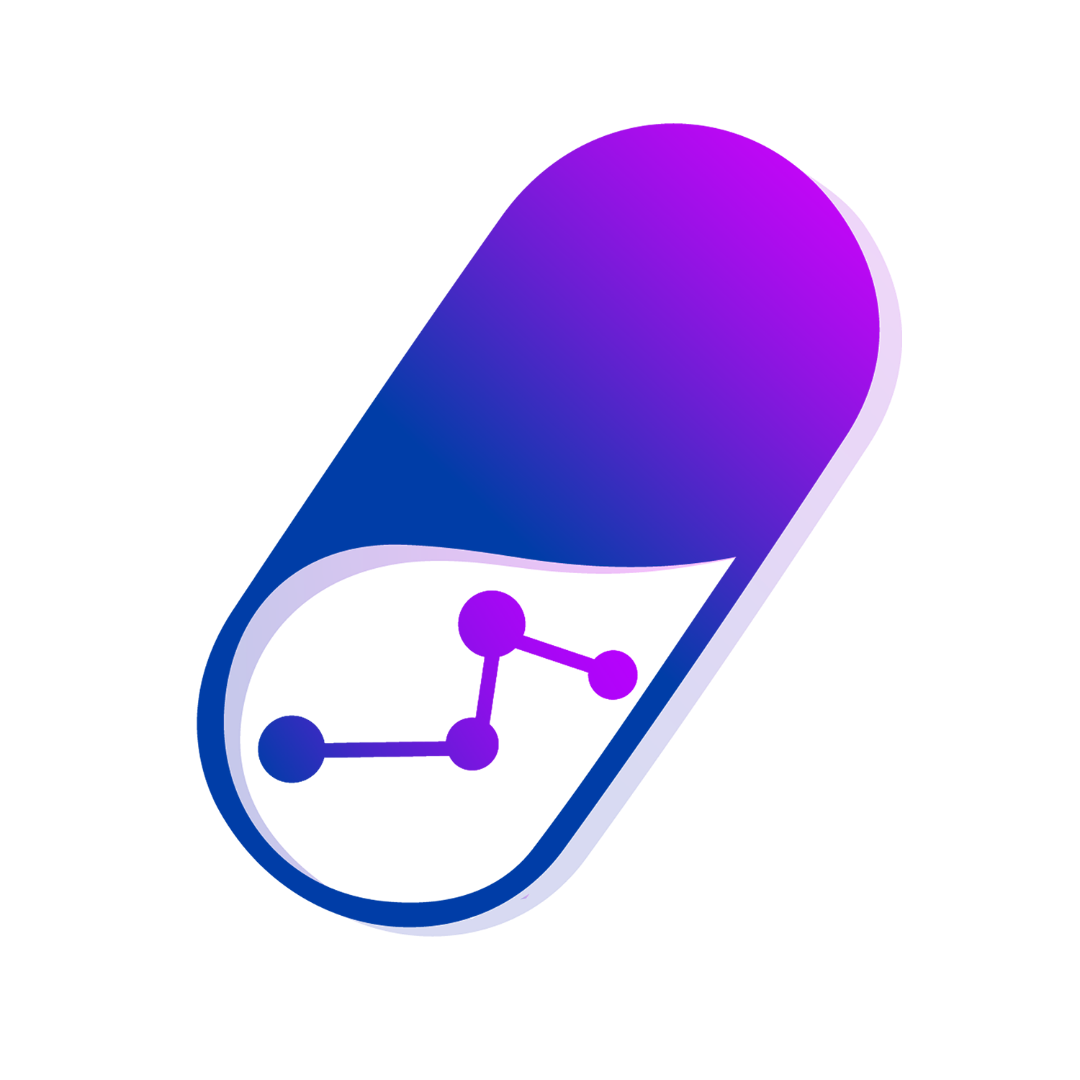 智药局
智药局
业界已经普遍接受了AI制药的说法,为什么哲源科技还要提计算医学?
赵宇:我们不会单纯地讲概念,AI制药是个应用场景,提计算医学其实是因为行业需要。计算医学是认知生命的新技术体系,它在底层逻辑上构建了对生命功能的理解和描述。而基于计算医学对生命的认知,应用场景既可以是制药,也可以是医疗,也会涉及到疾病的早诊和预防。
我们观察到,当前AI制药的核心是如何设计和发现成药性更好的分子,95%以上的AI制药公司集中在临床前研究。尽管这部分也有很大的价值,但我们认为当前药物研发的痛点已经开始转移。
按照当前的“内卷”程度,药物研发需要做差异化竞争,这意味着必须对靶点和适应症有独到之处。但实际上临床试验是行业的死亡之谷,不管分子优化得多么好,临床前研究多么充分,到了临床试验阶段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痛点问题,必须得有新的技术手段。计算医学首先就是根据临床上的行业和痛点提出的,是以疾病为直接的研究对象。
从可行性来讲,数据层面当前有 4000万篇的生物医学文献,以及人类的基因组、转录组、蛋白代谢等数据;算力层面,当前基础设施的算力包括云计算、超算中心等已经很发达;模型上也开始展现了智能化。
从行业需求以及技术可行性来讲,我们认为已经可以建立“计算医学”的技术体系,区别于以往AI+分子的做法,从疾病的角度去做靶点发现、药物研发、适应症拓展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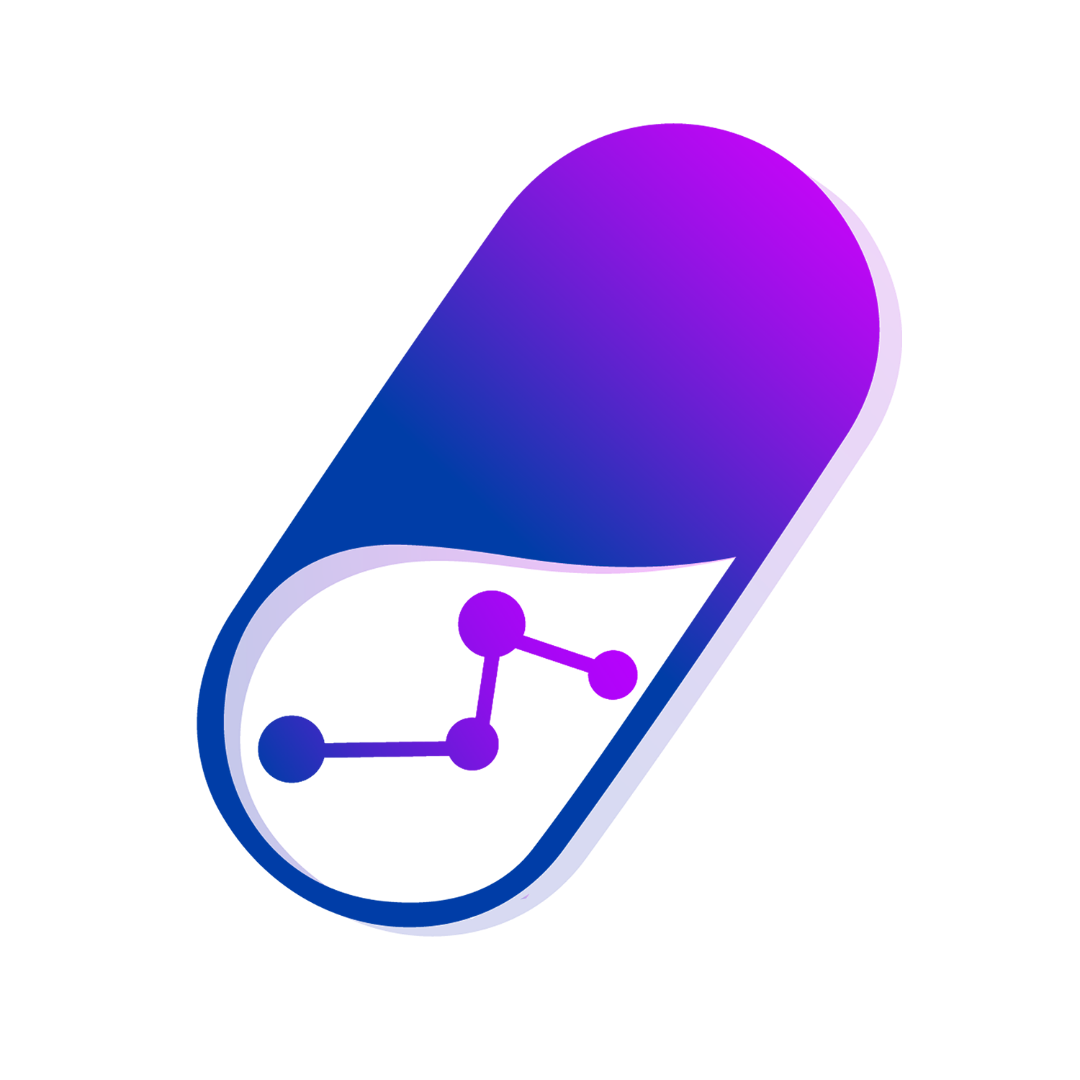 智药局
智药局
您去传播计算医学的理念的时候,例如跟企业去沟通或者要去寻求合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定的阻碍?
赵宇:还是会有,大家学科背景差别带来的理解差异。我们更希望从大逻辑理解,在结果导向下是否源自AI的发现其实关系不大。
跟药企合作的时候对方不太关心你是 AI 制药还是计算医学,它更多的是关心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样增量的价值。实际上你能告诉合作方一个很好的洞见,我可以告诉对方这是来自 AI 模型,我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灵感。
另外对方可能会关心洞见的可靠性,是不是有一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你这个洞见是合理的,只要说明这两点,其实没人关心这是AI发现的还是人发现的。
让我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内国际顶级的制药界科学家已经认可计算医学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带来的巨大价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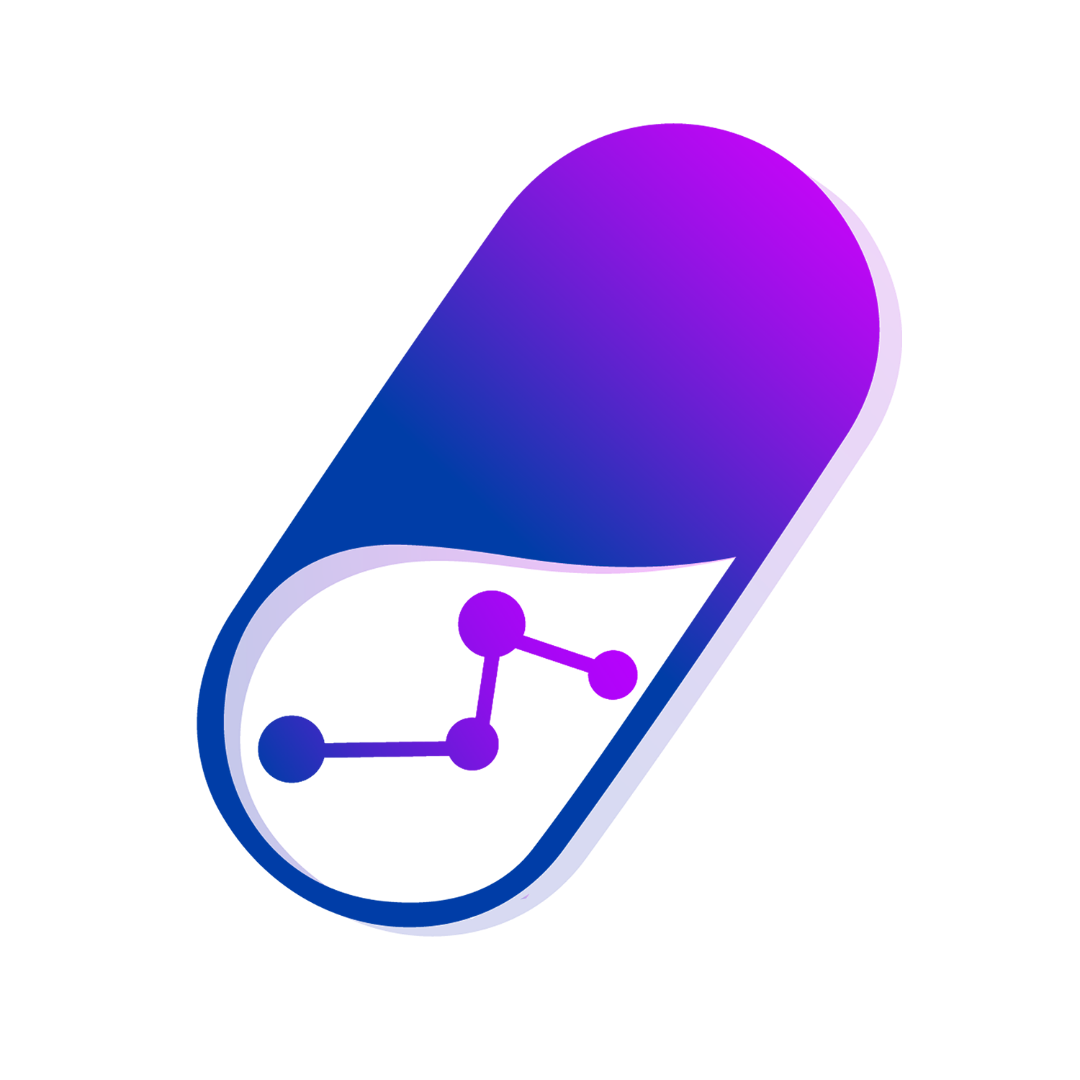 智药局
智药局
按照您的意思计算医学靠近临床更多,那么具体是如何做的呢?
赵宇:这就是我们团队的核心能力了,临床试验的难处就在于病人的状态太复杂了,因此很多因素都会导致结果的变化。
大家一直强调的MOA (药物作用机制)指导下的临床试验,但其实一直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实际上是,很多MOA是生物学家通过细胞实验或者动物试验发现的,可以说是理想状态下的MOA,在疾病条件下却未必成立,因为人体疾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和网络。
我们强调对疾病本身MOA的建模,而不是仅仅对分子的建模。计算医学是帮助大家以人体真实的环境为研究对象,将有价值的信息反馈出来。这些信息如果是临床方面的,可以加深对疾病的理解,如果是药物研发方面,可以应用于临床试验和靶点发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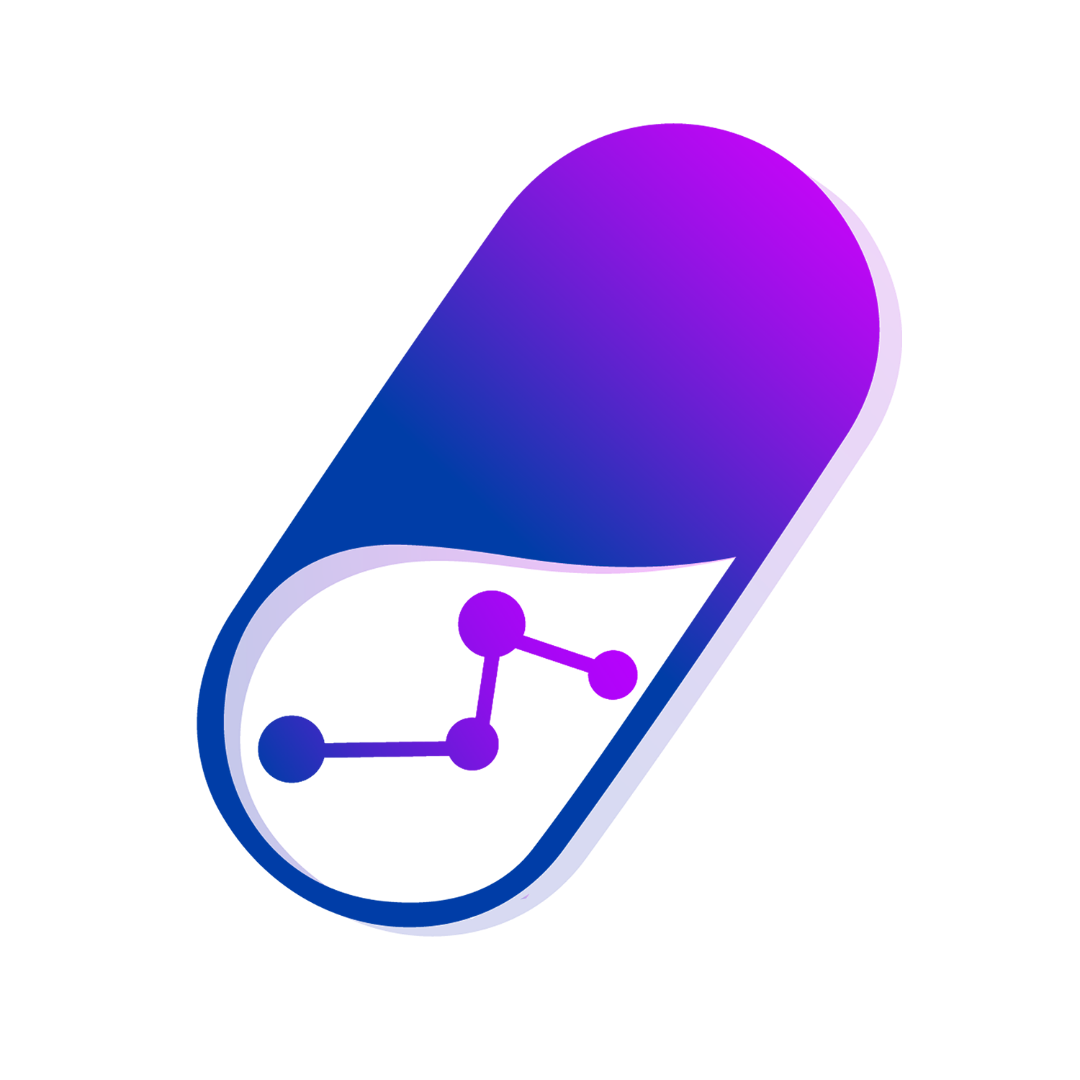 智药局
智药局
临床前AI模型两三个月内能得到反馈,与之相比,计算医学模型验证的方式和时间大概是怎样的?
赵宇:我们认为临床前AI模型完全没有得到验证,您所说的两三个月得到反馈是指候选分子的属性,距离临床试验是否有效还非常遥远,我们也看到AI设计的第一批分子临床大溃败。
而计算医学以疾病为核心,我们主要通过和医生的合作进行验证,毕竟“上人”是最高等级的验证。事实上对于疾病的理解可以通过两方面验证,一方面建立疾病模型对靶点进行研究,靶点本身有一套生物学验证体系。
如果已经有临床治疗方案,那么可以发起IIT试验,这部分验证的时间相对较短,基本上取决于规范化流程的时间。另一方面,可以基于RWD完成验证,对于临床上已经有治疗标签的患者队列,进行回顾性验证,盲测后与治疗标签对照验证。这两种方式我们这几年都已经有多项验证成果。计算医学的终极验证时间远远短于临床前AI模型的终极验证时间。
举个例子——老药新用,这些已经获批上市的药物拓展新适应症,我们预测出来A疾病的a 亚型上能用,同时该亚型又没有合适的治疗方案。这时候可以联合医生发起基于伦理的IIT实验,这就是计算医学非常经典且证据等级很高的一个验证方式和闭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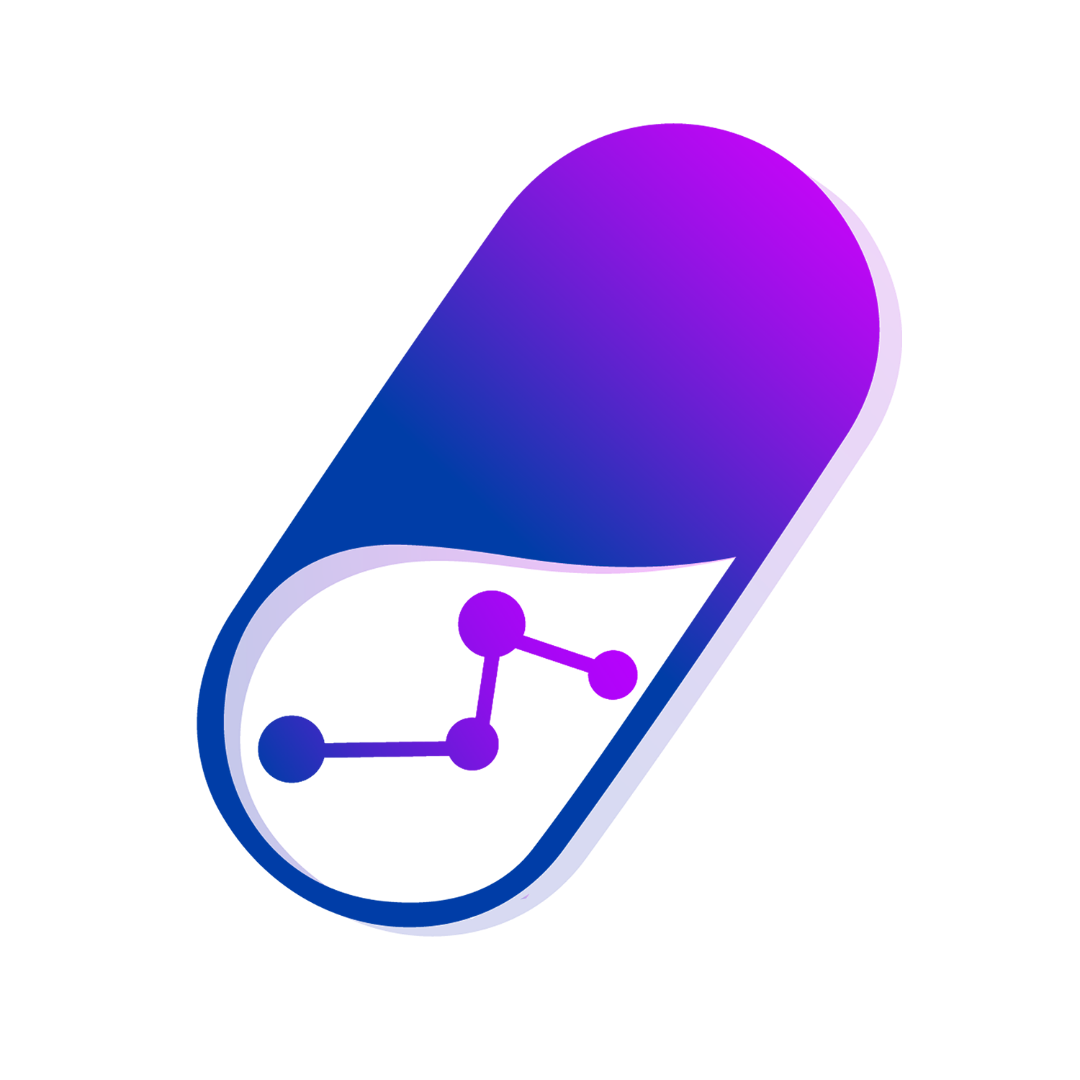 智药局
智药局
一种观点是,AI进入临床阶段能发挥的效用很低,您怎么看?
赵宇:其实全球顶级的团队已经在临床试验环节有很多优秀的落地工作,临床试验占到整个药物研发临床的时间和费用近八成,失败率超过90%,AI赋能临床价值和市场空间巨大。
AI设计和优化分子实际上在学科上是有迹可循的,可以追溯到计算化学,换句话来说是有学科体系的,人才不稀缺。但AI对于疾病的理解方面却缺乏基础,既难又缺少学科体系,需要深度交叉的团队才能实现。
我们认为 AI +临床这块应该有几个点要去做。第一方面,对临床数据的分析非常有价值,我们把它称为回顾性的数据总结。第二个重要的方面,能不能在临床阶段前瞻性地辅助做临床方案的设计,例如选择适应症和病人。
此外,临床试验的过程中,实验结果和已有模型调优和匹配的问题。临床前通过 AI 分析给出了适应症和人群特征,临床试验的过程中AI 仍然会收集数据,比对真实的结果和 AI 预测结果的偏差。根据偏差再将数据再输入模型调整, AI 能够伴随着临床试验同步进行,实际上它就介入了临床试验的核心环节,它所发挥的效能就是足够大,而不像现在主要作为一个回顾性的结果的统计。
 以IP为核心构建商业闭环
以IP为核心构建商业闭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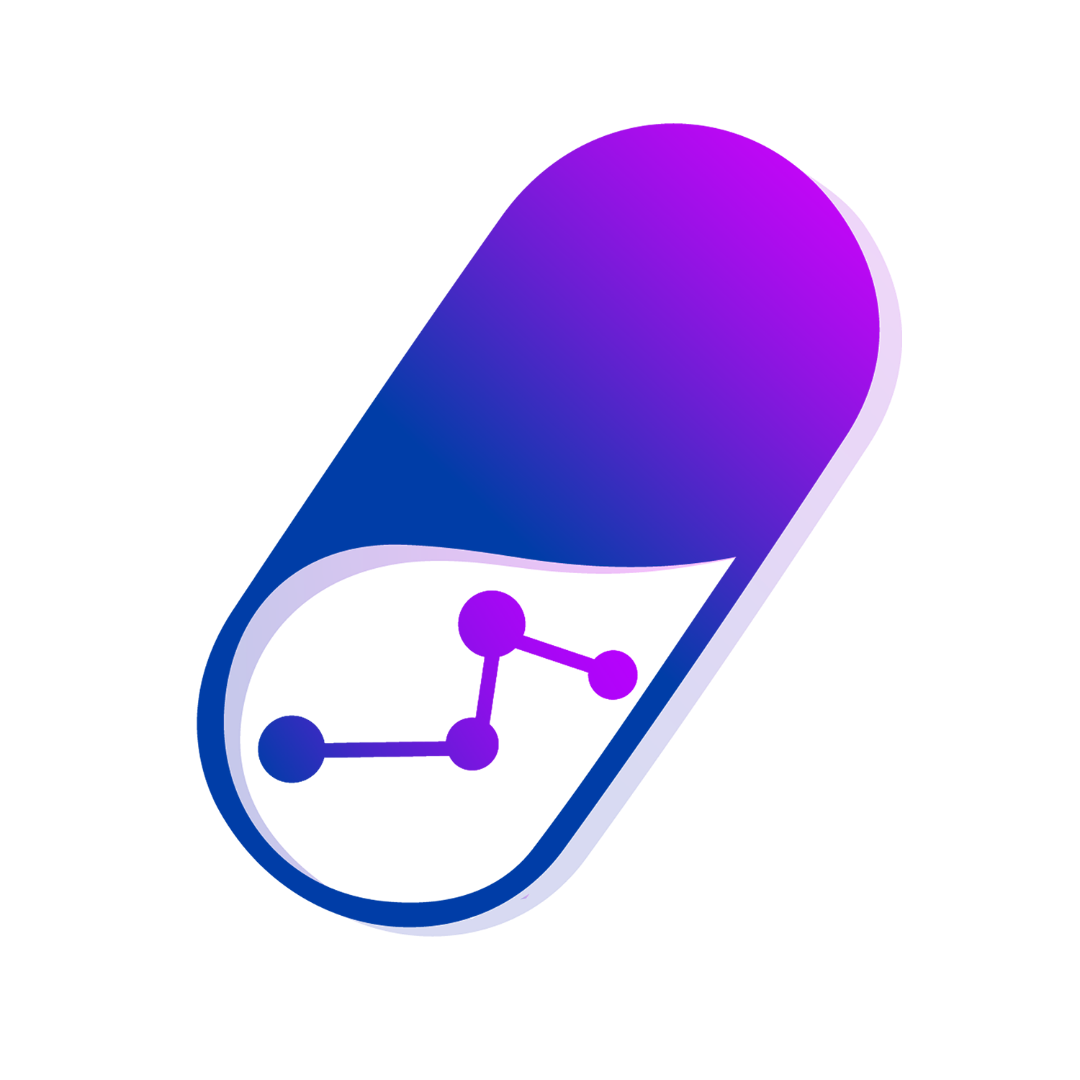 智药局
智药局
哲源是一个交叉度很高的团队,公司团队大概是什么样的构成呢?
赵宇:我们团队负责人是做超算出身,也有多年生物信息学的经验。团队的构成上,负责算法设计、高性能计算、以及药物设计、临床试验的都有。但核心是我们称之为总师型人才,这些交叉人才既懂生物也会设计代码,他们会提出问题并分解,接下来请各个领域的专业负责人来实现。如果一个团队里边没有交叉型的人把各个环节的人凝聚在一起,那基本上很难做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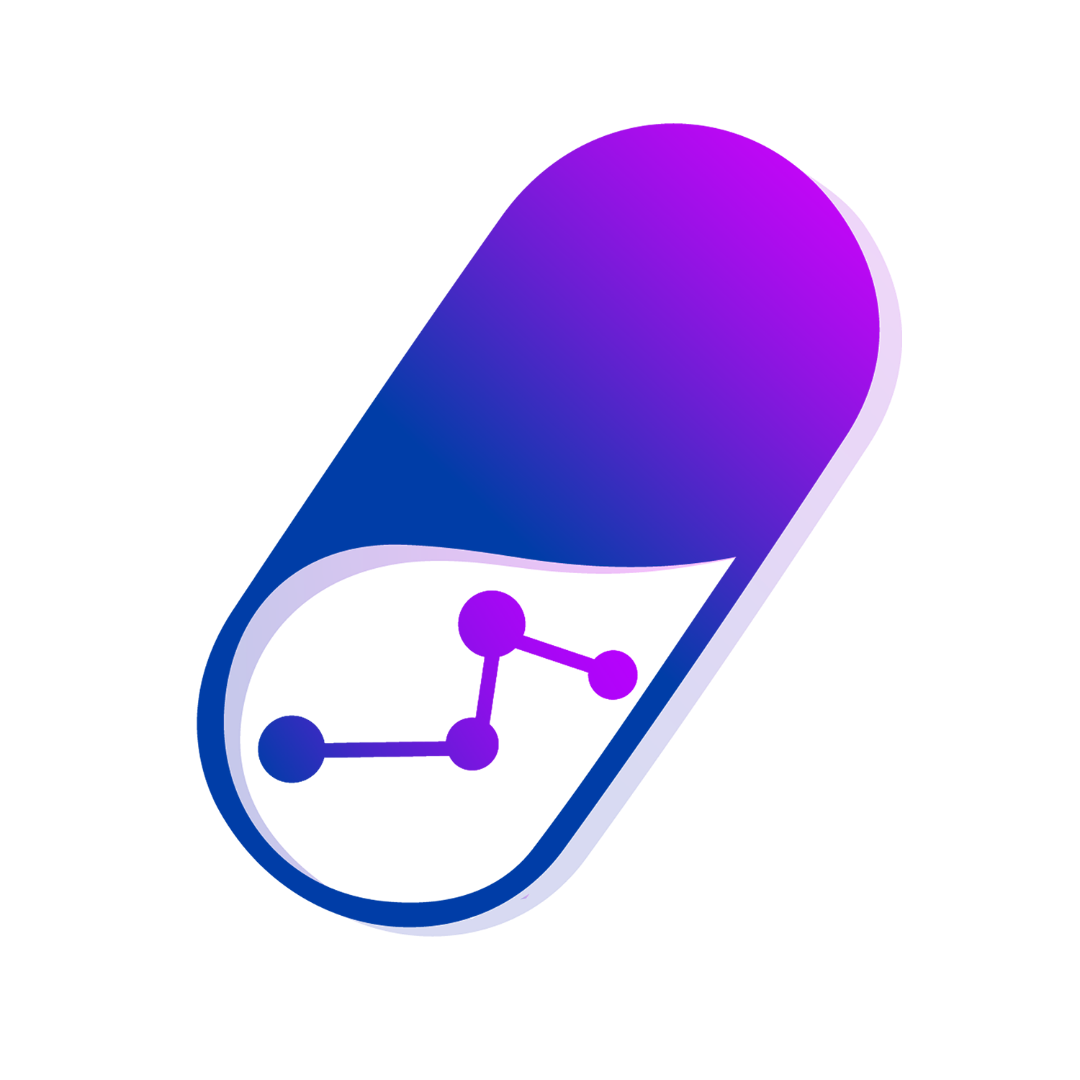 智药局
智药局
现阶段中国创新药环境仍然是风险厌恶型,大家还是一窝蜂地选择相同的靶点和适应症,力求绕开原研药的专利,即便您说的技术很有价值,但市场会有需求吗?
赵宇:风险厌恶的结果就是“卷”,都想降低临床试验这一“死亡之谷”风险,的确当前中国药企绝大多数follow别人的靶点和适应症,在别人的基础上去探索可以把风险大大降低。
但实际上带来一个问题:技术上的确降低风险了,但商业上是否成功是个未知数。因为很多人会发现按照这种模式,中国创新药就变成了比谁follow得更快,包括大家一窝蜂地选择几个靶点后还面临着后续销售的问题。
举个例子,中国在临床阶段的CDK4/6抑制剂应该有30个左右,大家都选择乳腺癌为主的一个亚型,再适当进行扩展。但是使用计算医学技术,我们能够帮助药物在适应症上做出差异化选择,和优势人群选择。
通过这样的逆向决策,药物研发的风险就变成了能不能满足临床需求,而不是获得一个绕过专利的合格分子,分子只是临床价值的载体。以分子为中心的决策方式只是让公司更容易立项,但后续商业上会在“内卷”的路上越走越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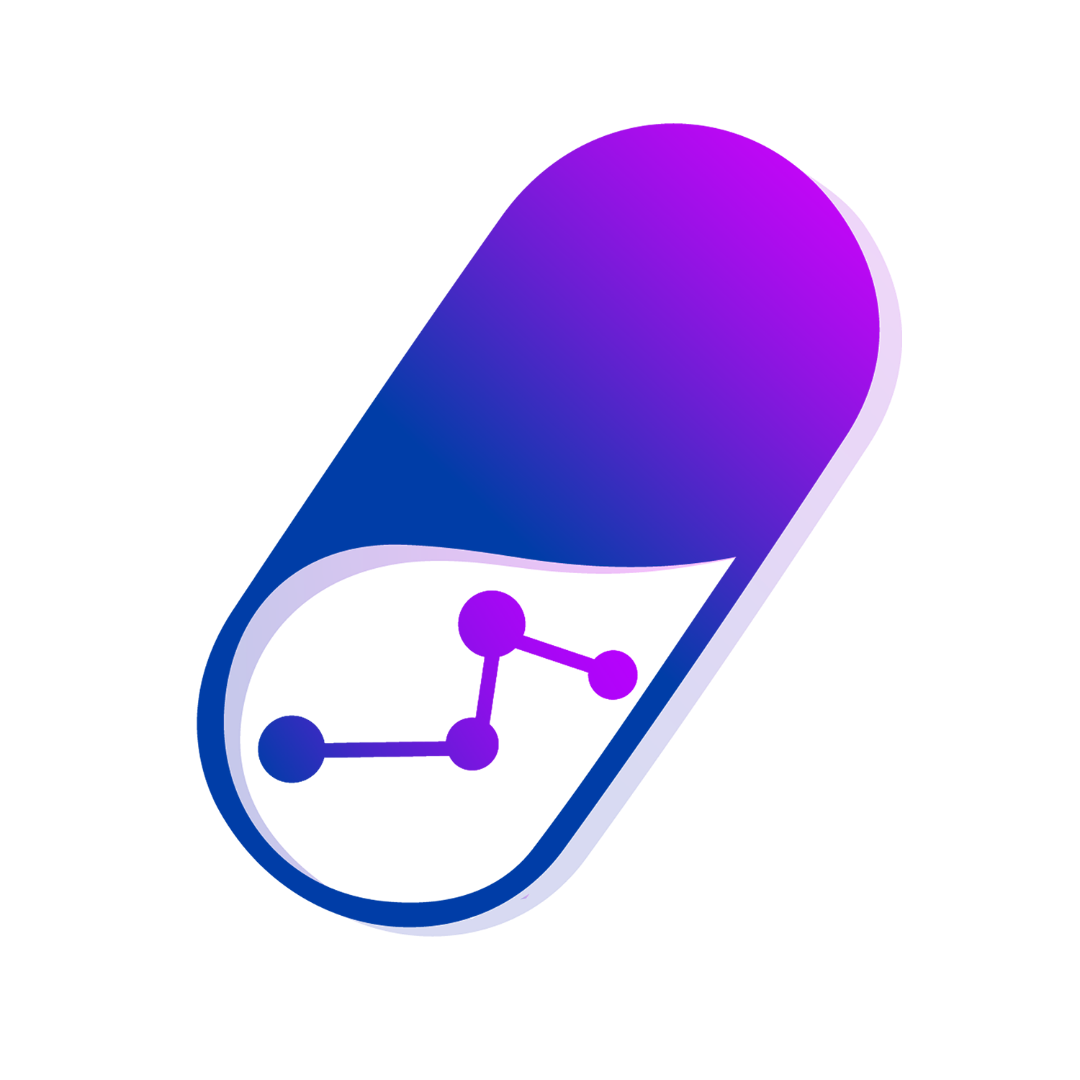 智药局
智药局
从计算医学的角度,能不能介绍一下公司的商业逻辑?
赵宇:其实我们的本质是运用AI去理解疾病,驱动药物研发和赋能临床试验。我们的技术路线是明确的,但商业落地还需要考虑产业土壤。
海外也有和我们技术路线相似的公司,正在和辉瑞、赛诺菲等跨国巨头合作,因为这些MNC本身就有原创性的需求,选择以技术服务的方式引进新动能。
尽管近年来国内药企对技术服务不那么排斥,但我们认为外输出IP,市场接受度会更高。所以我们对哲源的定义是药物的 IP工厂,IP资产实现对外授权。
我们的IP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IP叫做已有靶点的新药IP。例如该靶点已经获得验证,通过计算医学找到该靶点新的MOA,或者新的疾病下的适用人群特征,在差异化的适应症上和人群上能获得收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冒仿制药的风险,拿到First in Class的收益。
第二类是相对全新的IP,选择的靶点本身具有新颖性,通过计算医学花费更少的钱和时间推进到临床,并且在临床过程中不断地验证验证和反馈,将临床入排条件优化得非常好。
那么哲源科技对外授权的时候,输出的不是简单的分子,而是 IP 的整体解决方案。它不仅仅是可专利的分子,还会包括临床条件应该是什么,我们相信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改变。
因此这种模式考验哲源科技快速产生批量化、差异化 IP 的能力,现在计算医学平台经过近20年的技术积累,其成熟度已经达到工业化水平,可以做到高效产出差异化IP资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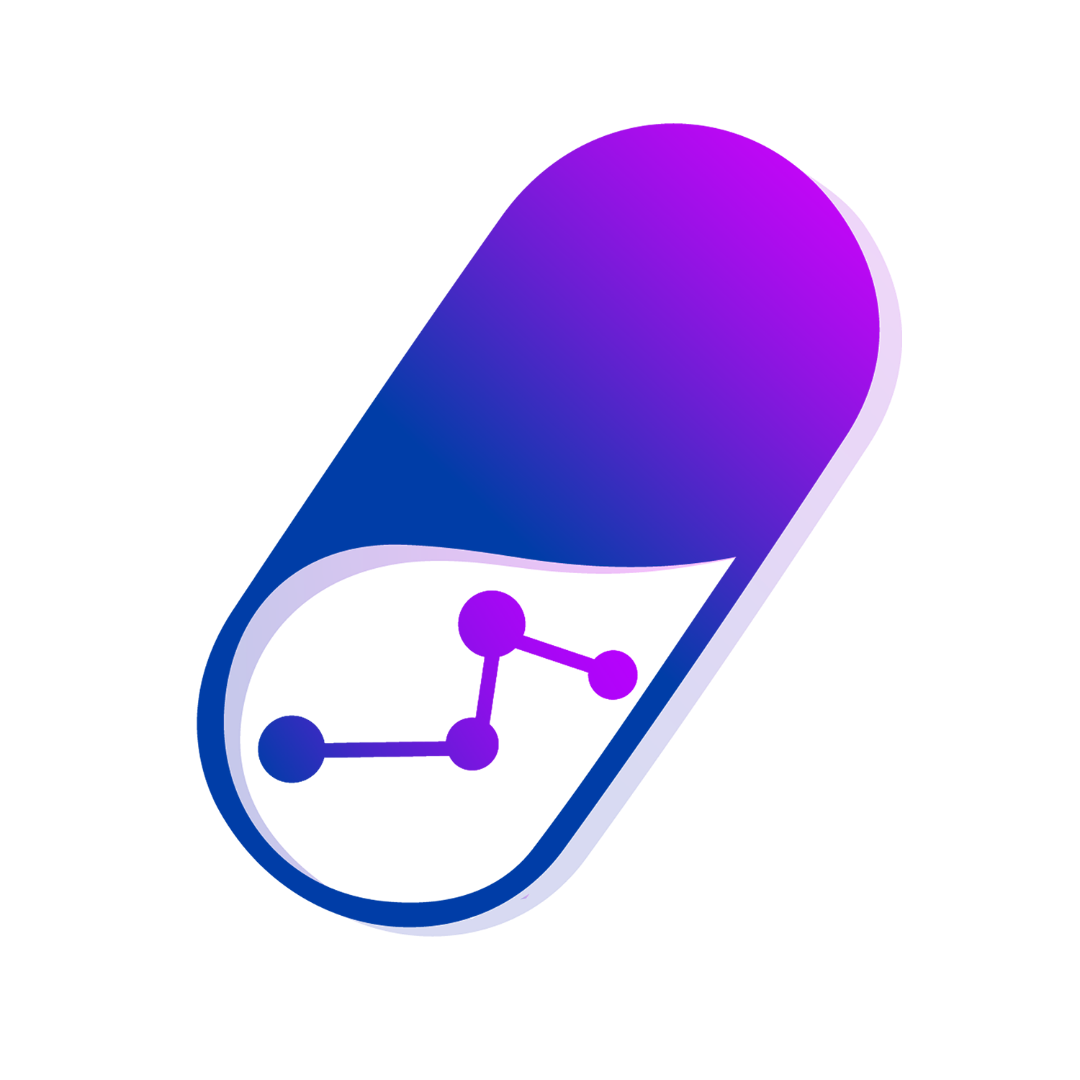 智药局
智药局
您一直强调IP的重要性,目前哲源的管线和IP的进展如何?
赵宇:哲源的每一个IP都是瞄准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解决原有技术体系下,高试错成本研发困境。我们自己进展最快的药物已经在IND-enabling阶段,覆盖到胰腺癌很高比例的患者人群,并且后续几个管线都是非常独特,且风险非常可控。
同时哲源储备了大量的靶点,我们很有信心它一定会走到临床并会取得巨大商业成功。向合作伙伴对外许可,我们也会坚持以首付款+里程碑+销售分成的商业合作模式,这也有助于我们储备的洞见更快地转化为新的IP。
—The End—
推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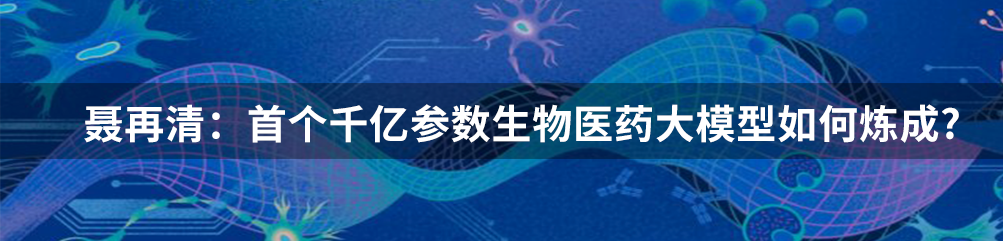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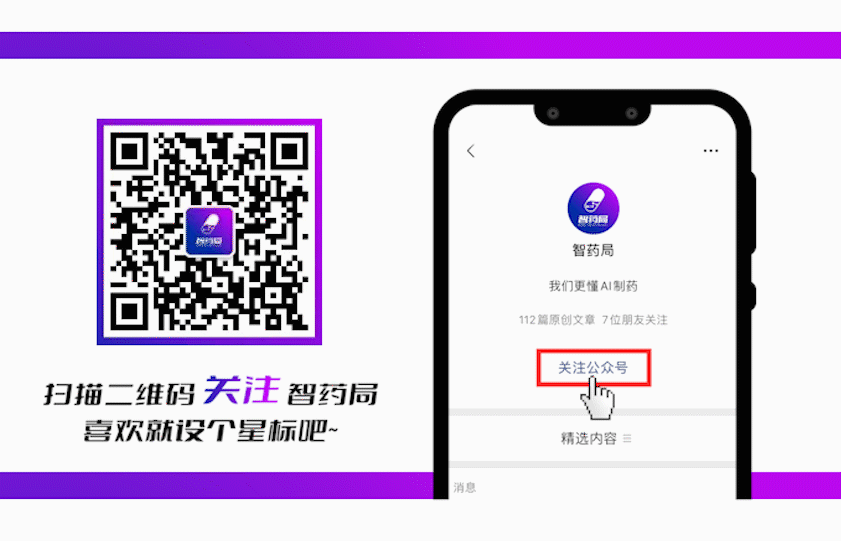




 ufabet
มีเกมให้เลือกเล่นมากมาย: เกมเดิมพันหลากหลาย ครบทุกค่ายดัง
ufabet
มีเกมให้เลือกเล่นมากมาย: เกมเดิมพันหลากหลาย ครบทุกค่ายดัง


